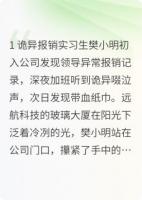封皮上用柳体端端正正地写着「三兄亲启」几个字,落款是「啸天拜」八个小字。信的内容却很简单,「与弟别又三年矣,每每闻弟之事,不禁心向往之以至辗转难寐。中秋将至,天气转凉,鸿雁高飞,渴慕之情愈甚,望弟能亲移贵履,至贱所一聚,畅谈天下英雄,兄弟别情,当月长歌,临泊鸣琴,其乐可期乎。」
张文远失望地摇了摇头,这不过是江湖痞子们拉帮结派,四处结交的把戏而已。他不是江湖中人,不曾听说过「啸天」这个名字,猜想最多不过是个粗鄙的土豪罢了。
这个时候,脚步声响起,有人在门外敲门,他赶紧把书信塞入招文袋,拉开房门,却是朱大爷,提着个热气腾腾的大铁壶,问他要不要热水洗漱或泡茶,张文远摇头说不需,他来之前已经洗漱过了。
朱大爷探头往屋里张了张,嘿嘿笑道:「我没有说错吧,张押司,你屋里都要长霉了吧!」他仿佛很高兴,笑得黄牙暴露,一嘴的臭气扑在了张文远脸上。
张文远退后一步,问道:「县爷起来了吗?」
朱大爷答道:「刚起来,正在花厅喝茶呢。」他说着,转身走了,又去敲隔壁的门。
张文远环视着这间几乎空荡荡的房子,自己在这里待了四年,最美好的青春之梦也是在这张床上梦见的,他叹息一声,从枕头下摸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匕首,揣入怀中,然后对着墙角的几张蛛网挥了挥手,转身出门而去。
张三兄弟
内衙的大门已经开了,两个下人正在打扫地上的落叶和积水,扫得哗哗作响,丝毫不理会过往的行人。
张文远央门边的听差去给县爷传话求见,听差正在啃一个粗面馒头,腮帮子鼓动着,含混不清地答道:「相公刚吃完早餐,正在书房练字,谁敢打扰他?」说完,背过身去,专心地啃馒头,不再理睬。过了一会儿,他感觉到没有了张文远的声息,转过身来一看,张文远早就窜进内衙去了,他狠狠地一跺脚,「这个死白三,不是害我挨罚吗!」赶紧愤愤地追了上去。
等他穿绕过几处回廊和墙院赶到了书房时,就见房门紧闭,但里面传来了张文远和县爷的对话。
「文远啊,你也算是块好料,能文能武,家学渊博,非其他书吏可比——就是人年轻些,容易感情用事,对于辞职这么大的事情要多考虑考虑。」
「大人,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。我只有离开,大家才好过一点。不然——不出半个月,我被谁捅死的都不知道。」
「胡说!」
「大人为官清正,作事廉明,只可惜新任此县,被一些人给蒙蔽了,以致阎婆惜一案有意开脱宋江,胡乱断案……不说了,小人告辞,大人多加保重!」
「你,你……」
时文彬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
门帘一挑,张文远满脸通红地奔了出来,正撞在目瞪口呆的听差身上,听差哎哟一声,嘴一张,半个馒头飞落,人也踉跄几步,快要栽倒时,被张文远扶了一把,才立正身子。
等他骂骂咧咧地把馒头拾起来,张文远早就消失在了回廊叠院之间。
灰黑的天空露出了东一块西一块的红蓝底色。
郓城知县时文彬的脸从门帘探了出来,目光深沉地凝望着张文远奔去的方向,沉思不语。
天光斜射在他白净的脸上,显得有些惨白,仿佛死人脸。
奔出内衙,穿过仪门,鞋底踏在甬道的石板上,溅起水坑中的雨水,啪啪脆响。